清初,温州江心孤屿遭盗匪霸占,僧人外出躲避,寺院遭到肆意破坏。某天一早,人们发现盘踞在寺院的匪徒突然消失了。据说,前夜宫殿里的青狮塑像显灵,变成了活物,张开血盆大口要吃人,匪徒吓得屁滚尿流,连夜逃离。可是,孤屿周遭只有江水滔滔,又哪来目击者传话?盗贼的离奇消失或许只是臆想,毕竟可能是正常撤离,也可能遭遇意外歼灭,还有可能与出身行伍的寺僧释元奇相关。
杜维德(Edward Bangs Drew)拍摄温州江心屿,1876-1880
少年从军,明亡出家
释元奇,字月川,明开国元勋刘基十二世孙,其俗名已不可考,以下统称“元奇”或“月川”,曾任清代江心寺第三任住持,主导修复江心屿古迹,出资刻印《江心志》、重刻刘伯温文集等。《江心月川禅师塔志铭》(以下简称“月川塔铭”)记载其简要信息,元奇父亲叫刘世源,其生母李氏,家中排行第二。注明生母,也意味着还有嫡母或继母,可以推断元奇不是贫寒人家出身。
时值清军南下,南明势力节节败退,福建地区成了主战场。元奇父亲出征,家中长子或嫡子没有同行,年仅十四岁的元奇跟随父亲到福建前线,其间艰辛不得而知。顺治十年(1653、南明永历七年),元奇脱离抗清军队,寄居温州护国寺,之后在福聚寺(或为今梧田福聚寺)剃度出家。顺治十七年,元奇在密印寺(今南瓯海头陀寺)随法幢行帜(俗名林增志)受具足戒,立志苦修佛法,参与修葺寺院、整修佛像,广受信众好评。康熙十三年(1674),元奇来到江心寺,皈依于清代首任住持体印明瑞座下。
《江心志》书影
笃行不怠,重振古刹
江心寺位于的江心孤屿,地理位置独特,原为东西两岛对峙,江水贯穿其中。唐咸通七年(866),江心岛的东山下始建“普济(寂)禅院”。一百年后的宋开宝年间,西山也建起“净信讲院”。建炎四年(1130),金兵进犯,宋高宗等浮海南奔到温州,曾登岛驻跸普济院,今江心寺内立有“高宗道场”碑。南宋绍兴年间,蜀僧真歇清(青)了奉诏住持江心两座寺院,开坛讲经,一时受众云集。但两寺之间江流阻隔,往来极为不便。某年川流淤塞,清了禅师亲率僧众抛石填川,将两岛连成一处,又在所填位置上创建中川寺。后敕改中川寺为江心寺、普寂禅院为龙翔寺、净信讲寺为兴庆寺,三寺从此统称“龙翔兴庆禅寺”。其间,清了禅师发愿开井,凿出了淡水,“海眼泉”至今尚存。宋元明之间,岛上寺院屡有兴废,明正德年间重建江心寺。

江心寺“高宗道场”
康熙十二年(1673),清廷下诏撤“三藩”,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清。次年三月间,靖南王耿精忠又在福建举兵响应,也称“耿乱”。三个月后,其麾下曾养性部已占领温州地区,元奇在“耿乱”这年来到江心寺。再下一年八月,住持体印卷入耿精忠和清廷的斗争,被曾养性抓获处死。江心寺群龙无首,寺院又遭兵匪霸占,元奇及众僧只得外出躲藏。
康熙十五年(1676,丙辰),耿精忠一方逐渐失势。九月,耿精忠遣子献印请降;十月,清廷派康亲王杰书率部抵福州,耿精忠出城投降;随后,曾养性于温州投降。
“耿乱”平叛后,百废待兴,物价飞涨。江心寺经历战火,寮舍破败不堪,元奇带头募捐,发愿重修江心寺。当时岛上有数十株古樟树,层层绿叶如亭亭华盖,数百年来掩映江浒,荫蔽寺院。战后物资稀缺,古樟树难免惹人注意,于是就有兵丁登岛砍树取材。元奇手无寸铁,却毫不畏惧,拼死力争,制止了砍树并说服兵士离开。已被砍倒的樟木,则被用在数十间僧寮等设施的修缮。简单修葺后,寺院已能正常运行,剩下大殿还没恢复。经此一事,元奇声望渐长,当时寺院住持空缺,他就成了实际的领头人。
没多久,禅宗临济宗高僧大云本莹游历江心寺,目睹古刹风雨凋敝,不禁感慨“此地为真歇了师道场,荒芜五百余载,惜无再立刹竿者”。元奇得知本莹禅师所言,大为感动,何不请禅师留下?于是他动员时任温州总兵陈世凯、知府王国泰,以及乡绅等人一起发力,恳请本莹禅师接任住持、振兴古刹。本莹禅师应请驻锡并升座讲法,好评如潮。本莹是重庆人,清了是绵阳安昌人,他们都是蜀人。因此,信众纷纷议论,这情形仿佛是清了禅师再临孤屿。当然,众人也认为元奇功不可没,靠他慧眼识珠、全力挽留才有此局面。
高僧住持古刹,让募资修缮大殿变得更加顺利。很快,更换大殿栋梁、重塑佛像金身,整个寺庙焕然一新。与此同时,元奇恭执弟子礼,每日晨昏问候,细心侍奉本莹禅师。三年后,本莹将衣钵传授给元奇,动身返回杭州东园寺(净慈寺)。后本莹禅师圆寂,元奇难抑悲痛,匍匐倒地,将本莹灵骨塔迎回温州,对待恩师始终如一。
另外,元奇还受托主持重修江心屿上的卓敬祠,指示弟子成宏、徒孙大增重建瓯海茶山龙潭寺旁妙智、广济两寺。元奇在当时温州留下诸多实物,但如今都消失无踪。
诗词唱和,留存文脉
元奇出身行伍,却非粗鄙之人,而是诗文、佛法全都通晓。《江心志》收录当时文人写给元奇的诗,如温州总兵官李华《赠月川和尚》,清初榜眼、明史纂修官李仙根《送月川和尚归江心》,清代画僧、文徵明玄孙释超揆《江心赠月川法兄》等等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立夏前一日,经学家王复礼(号草堂)在江心屿举办了一场三十多人参加的“江心雅集”,众人诗词酬唱,其中就有元奇所作七言诗《与王草堂居士》。
与王草堂居士
释元奇
瓯江江上卧龙起,啮断中流涌双峙。
嶙峋楼阁拟蓬瀛,江树江花媚江沚。
有客遥来自琅邪,携朋载酒共坐花。
高歌满座晴飞雪,逸兴浮杯昼落霞。
霞光片片辉贝叶,色映火云云千叠。
须臾布地似黄金,晚烟江上催归楫。
嗟予十载掩禅关,客到无心自往还。
蒲团夜静吟初就,明月光浮水一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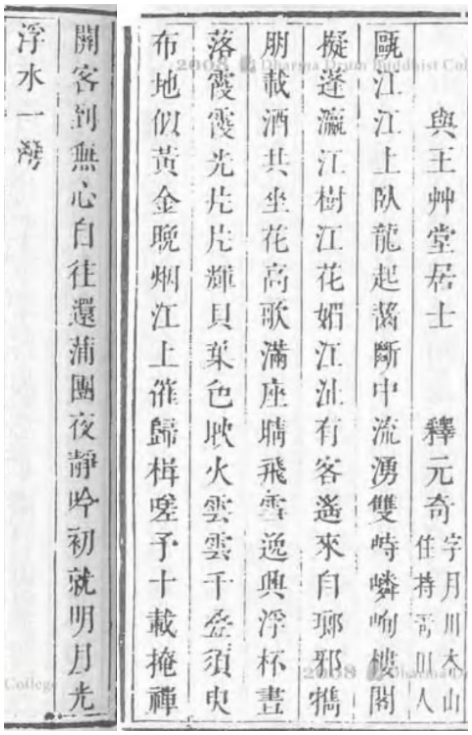
《与王草堂居士》诗
康熙三十九年(1700)腊月,元奇受推举就任住持,化用唐代诗人王之涣名句,将孤屿、瓯江、双塔等景物融为一体,口占禅诗“孤屿花如锦,中川水似银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最高层”,随即开示“欲识佛性义,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若至,其理自彰。且作么生是自彰之理?”此后,元奇应邀去平阳宝定院解说《戒结制》,现场学者叹服其佛学造诣。
温州江心孤屿人文荟萃,明代编纂刻印多件《江心志》,康熙年间元奇又出资增辑并刻印《江心志》十卷。元奇所辑《江心志》分为纪迹、敕书、艺文、世系、杂记等,体例更加完备,内容更加丰富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)夏,时任浙江学政彭始抟为其作序,称赞元奇为江心屿所作的贡献,“月川禅师不惜己费,为孤屿谋不朽,其功匪小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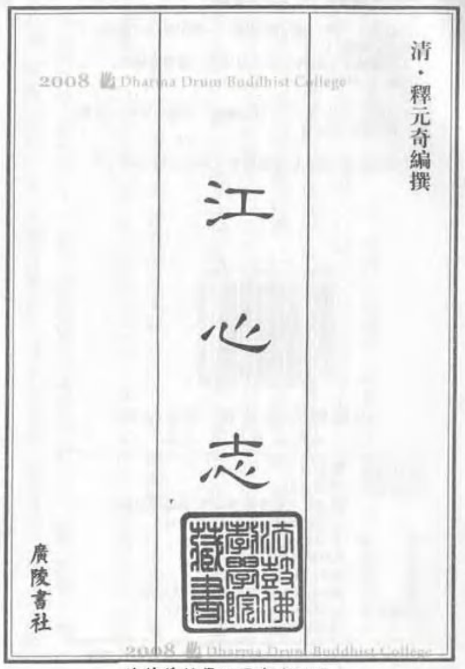
《江心志》书影
这年秋天,彭始抟还作有《诚意伯刘公赞》,收进元奇捐资刊刻的刘基文集卷首。重刻刘基文集的机缘始于一次偶遇:元奇在江心寺遇到陪儿子读书的刘标。交谈中发现,他们都是刘基后裔,年迈的元奇却是刘标的子侄辈。刘标是温州城里人,家住新河里(今信河街一带),是康熙年间岁贡生,祖藏一件隆庆年本刘基文集刻本。刘标有心翻刻先祖文集,但又无力承担刻书费用。元奇决定捐出毕生积蓄,用于重刻《太师刘文成公集》二十卷。
可惜书还没刻成,元奇便溘然长逝,刻书一事也因老和尚圆寂搁置。之后,书版的流传经过颇为坎坷。先是雍正年间,青田知县万里捐出一年俸禄,委托温州刘标后人补刻未完成的第十一至十八卷,完成元奇未竟事业。再是乾隆年间,刘基十四世孙刘沛斥资,将书版赎归刘伯温故里南田。乾隆年间青田县令高居宁为重印本作有序言,称赞刘沛这一壮举,但没发现刘沛的心机。刘沛持有书版时,曾将各卷开头书版上的温州宗亲姓名悉数剜去,只保留元奇及南田参与者信息,但在无意中又留下了刘标等人零星信息。这批书版几经修补,直到民国初年还在使用,印制的刘基文集流传极广,最后消失在温州书坊火灾里。
光前裕后,蛛丝马迹
清末浙江官书局翻刻南田所藏《太师刘文成公集》,相当于书版火毁前做了一次备份。一般来说,出家人是不能记入宗谱的,但《南田刘氏宗谱》破例收录了月川禅师小传。这是因为元奇重刻祖先文集居功至伟,“夫出家,谱不书名,兹何以书?以其能存先人之手泽故书之,以志有功云。”饶是如此,元奇本人出身情况实在稀缺,只有些许同时代宗亲或嗣法传承线索留存。
元奇和温州城里的刘基后裔应当有往来,《太师刘文成公集》雍正续刻本卷首校阅者名单里就有三位“东嘉裔孙”也在《江心志》留下诗作。如排首位的刘世灏(字殷书)、第三的刘琦(字声如)、第五的刘振瑄(字汉珍)。以此可见,温州城区在清初有刘基后裔聚居,其中不乏读书人,也可推测家境殷实、人数不少,但当前温州信河街一带没有留下线索,信息就此中断。
查考元奇相关联的数名高僧身世,大多与抗清志士有关系。按顺治八年二月,皇帝下谕“以后僧道永免纳粮,有请度牒者,该州县确查呈报司府,申呈礼部,照例给发。”由此,参与抗清、不愿降清的志士纷纷选择出家。
和元奇关系最紧密的高僧是法幢行帜。释行帜(1593-1667),字法幢,俗名林增志,字任先,瑞安人,少时曾读书密印寺,明崇祯元年进士,是明遗民遁迹丛林中最负盛名者之一。隆武二年(1646,顺治三年),林增志任文渊阁大学士、礼部尚书,随驾移镇建宁、延平;隆武死难,林增志逃至沙县,出家并取法号法幢。顺治五年(1648),法幢回到温州旧日读书的密印寺,只见寺宇行将倾圮,矢志予以修复。顺治八年(1651),前往处州募缘修寺,拜访南明寺、三岩寺、白云寺等千年古刹,途中还有游览青田石门洞,拜谒丽水开国元勋祠,留有《礼文成祠》“元士甘为中夏臣,知几望气独超伦。帝师算是刘侯胜,王佐甘如小友神。遗像须眉何脱落,旧时榱桷竟埋堙。我来瞻礼生悲感,搔首荒台忆隐沦。”次年,法幢嗣法于宁波雪窦寺石奇通云,定法名行帜。
高僧“弘觉国师”木陈道忞是本莹的衣钵来源,即元奇的师祖。他与林增志也有交集,但后来对反清复明信念有所动摇。释道忞(1596~1674),字木陈,俗姓林,广东大埔人,入清后先为遗民僧。顺治八年年底,道忞到温州与行帜会面,留有僧偈相对,言语中暗藏机锋,如道忞提到“须发尽除颜面在,林泉独对檗冰甘”,行帜对以“霜威扑面谁为受?缘会调心转自甘”。顺治十六年,道忞进京打醮说法,受顺治帝敕封“弘觉国师”,之后抗清思想发生大反转。
另有明末高僧“慧定禅师”密云圆悟,他是道忞和通云的师父,弟子也有坚定的抗清者。释圆悟(1566-1642),字觉初,号密云,兴复宁波天童禅寺,使临济宗得以中兴。当时皈依者3万余人,得法弟子12人,其中有多位弟子是明末望重一时的名僧。崇祯末年圆寂,康熙间追赠“慧定禅师”。圆悟的弟子黄毓祺(介子)居士志在反清复明,顺治四年,集结师徒,自舟山进发,起兵海上,约定常州五县同日起兵,结果未能成功,临刑前留有“不负先师”等语。道忞当时作有挽诗,《挽介子黄居士有序》“壮志未酬先蹉跌,百身我愿彼苍何。”
观澜索源,浅析身世
《月川塔铭》、康熙年间温州知府赵恒等,均言月川乃明诚意伯刘公之裔,但元奇之父“刘世源”却不见于南田刘氏族谱,其源流世系仍然是个谜团。对照刘基十四世孙、末代诚意伯刘孔昭行迹,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。
公元1653年,岁次癸巳,在清朝是顺治十年,在南明是永历七年、鲁王监国八年,也是元奇离开南明抗清军队的年份。这年三月,刘孔昭随张名振抗清,率航船入长江、破京口,最后驻扎厦门,中途泛海会经过温州。在更早之前,刘孔昭部已曾数次途经温州。如隆武元年(1645,顺治二年)八月,杨文骢、刘孔昭等屯兵处州、温州;次年六月,清兵攻入绍兴,鲁王自江门入海,命刘孔昭“严戢所部,毋犯瓯土。”从时间上看,元奇和刘孔昭极有可能存在关联。
康熙十三年(1674),“耿乱”蔓延到温州。此时,行帜已圆寂七年,元奇在这年离开密印寺转投江心寺。江心寺住持体印则是倾向清廷一方,他为关押在江心屿的清廷副将杨春芳送信,被曾养性部抓获处死。从抗清志士主导的寺院转到亲近清廷的寺院,应当是元奇出于躲避灾祸的需求。
元奇生卒年也是个谜,目前可推断他大约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(1638,戊寅),卒于康熙四十四年(1705)至雍正八年(1730)之间。《月川塔铭》记载“年十四随父之闽”,查考南明史料,南明势力入闽的时间大致有三条,顺治二年(1645,乙酉)闰六月,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;顺治三年(1646,丙戌)十月,郑彩迎鲁王入闽海,福建成为抗清主战场;顺治八年(1651,辛卯)九月,清军攻克舟山,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再次入闽。其中顺治八年(1651)张名振护卫鲁王入闽、元奇十四岁(虚岁)较为合理,即元奇大约出生于公元1638年。
对照康熙壬午(1702)《江心志弁言》提到元奇“年近古稀”,按元奇十四岁(虚岁,下同)“随父之闽”来看,出生时间大致也可有三种可能性。若元奇在1638年出生,则虚岁六十五,是较为合理的时间;用另两个时间推断,则会出现“年逾古稀”的矛盾。《弁言》还提到元奇“潜修五十余载”,按其剃度在癸巳(1653),作弁言的壬午(1702)时已出家49周年,尽管略有虚饰,但大致相符。另外,以此推测,元奇在癸巳(1653)、十六岁剃度成了“沙弥”,直到庚子(1660)、二十三岁受具足戒才成为“比丘”,其间相隔七年之久,但并无矛盾之处。按隋唐以来汉传佛教僧尼受具足戒,须年满二十,可见于《四分律》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裴国桢等为《江心志》作序,从文意可见,元奇应当健在。而雍正八年(1730),青田县令万里为补刻文集作序,元奇已圆寂多年。
元奇寿塔建在原永嘉县二十四都潮埠(今鹿城区藤桥镇潮埠村)北山。该处离瓯江不远,或许是为了能见到瓯江,可惜具体位置难以寻找。
结语
嘉靖十一年(1532),刘基九世孙、处州卫世袭指挥使刘瑜获得续封诚意伯,在南京五军都督府各军任职,后任提督操江一职。嘉靖二十八年(1549),刘基十一世孙、刘瑜长孙刘世延出幼袭爵,刘世延及其十子均在南京生活。
元奇嗣法自抗清志士出身的高僧,其行迹又与刘孔昭部当时行军路径相符,元奇父子或许出自刘孔昭阵营,与诚意伯刘瑜、刘世延等嫡长孙一脉亲缘较近。另外,元奇没有和家人联络,也没有与南田宗亲往来,大概率是出自南京一派。
参考书目
1.(清)释元奇辑《江心志》,康熙四十六年刻本
2.陈光熙编《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》,上海社科院出版社,2005.01
3.《太师刘文成公集》雍正补刻本、乾隆重印本
|

